祥林嫂到底表达了什么_祥林嫂到底因何而死
作者:汲安庆
祥林嫂因何而死,一直众说纷纭。
《祝福》中,那位鲁四老爷家的短工用不可置疑的口吻说:“还不是穷死的?”
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。祥林嫂被鲁四老爷家解雇,沦为乞丐,且饥寒交迫,完全有可能。但是,在死前的几个月,这个四十上下的女人还“默默的跑街,扫地,洗菜,淘米”,很富有活力;和四婶说捐门槛的事时,还“神气很舒畅,眼光也分外有神”。即使是死前的头一天,问“我”灵魂的有无时,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还“忽然发光了”。如此“阳气”尚存,怎么突然就死了呢?再穷,讨一口饭,特别是在各家各户食物比较充沛的年关讨一口饭,以维持生命机体的正常运转,应该不难做到。所以,“穷死”一说只看到了表面,并未涉及根本的原因。
后世学者多套用毛泽东的理论,将祥林嫂的死因归结为“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”这四大“绳索”的束缚。鲁四老爷代表政权,婆婆代表族权,地狱代表神权,祥林代表夫权,各种势力交相压迫,于是祥林嫂被“绞”死了。
这种说法颇具权威,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盛行,至今还余威尚存。但细究起来,依然牵强,生硬,有些地方甚至还很荒谬。
鲁四老爷虽然对祥林嫂没什么好感,但也仅是“皱了皱眉”而已,还不是当着祥林嫂的面。是出言不逊了,骂祥林嫂是“谬种”,但这已经发生在祥林嫂死后。这种情况,按照孙绍振的说法,即使是1949年以后“镇压反革命”,或者“清理阶级队伍”,“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”都拿他没有办法,因为这只是思想意识问题,不是人身侵犯。[①]更何况,祥林嫂干活,鲁四老爷付工钱,你情我愿,也谈不上迫害。即使开除祥林嫂,也完全合理。总不能白养一个丢三落四,近乎失去劳动力的佣人,也不是开慈善机构,仅凭“皱了皱眉”就说人家束缚、压迫、摧残,还代表了“政权”,未免上纲上线得有些离谱。
象征族权的婆婆确实是压迫了祥林嫂。采用暴力手段,强行将祥林嫂绑架,卖给贺老六为妻,净赚八十千。除去替二儿子娶媳妇花财礼的费用,办喜事的费用,还剩十多千。另外,祥林嫂做工所挣的一千七百五十文一股脑儿都被她独吞。说她压榨、欺凌、摧残,不把祥林嫂当人看,一点都不为过。不过,她没有将祥林嫂压迫致死,反而意外地让祥林嫂活得更滋润了——与贺老六生了儿子,自己胖了,儿子也胖;上头又没有婆婆,丈夫有的是力气,会做活;房子是自家的。用卫老婆子的话说是“交了好运了”。所以,“族权的束缚说”也需要再推敲。
至于夫权的束缚,更是没影的事了。小说中,没有一句写到祥林对妻子的压迫——贺老六也没有。不错,夫死要守节,这委实是夫权的残酷之处。祥林、贺老六没压迫,不代表夫权观念没压迫,周围持这种观念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没压迫。问题是,祥林嫂对此心甘情愿地认同,还誓死捍卫,把脑袋都撞出一个洞了,血流不止。仅凭这一点,“夫权束缚致死说”就会不攻自破!
“神权束缚说”其实也难以成立。因为小说中没写到一个神摧残祥林嫂,倒是一个虚构的阎王让祥林嫂深感恐惧——据说阎王会将她锯为两半,分给两个死鬼男人,这个所谓的终极审判使祥林嫂的劳动力、记忆力迅速走向轰毁,并最终走向了死亡。为合理起见,最好说是“鬼权束缚”。
但这依然难以立足。因为这阎王不是自己找上门来摧残祥林嫂的,而只是柳妈嘴中的虚拟鬼,祥林嫂的心中鬼,发挥了折磨效力。仅凭一个荒诞的念想,还张冠李戴,将罪名扣在虚无的神身上,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。
源于此,孙绍振的“观念吃人说”显得比较客观——祥林嫂是被封建礼教观念以及对女人和寡妇的成见与偏见吃掉的。她悲剧的特点是没有凶手,是没有刽子手的死亡,她是被一种观念逼上死路的。[②]钱理群先生与之同声相应,将之归因于“看客的麻木和残酷”,“咀嚼鉴赏祥林嫂的痛苦”,成为“渣滓”后,立刻“厌烦和唾弃”,施以“又冷又尖”的笑,祥林嫂是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祭坛上的牺牲品”。[③]这结论很类似于刘再复先生所说的“共犯结构”,是人处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成为“结构人质”的悲剧[④],是一种对个体生命的群体性猎杀,但又不是有意为之的硬性暴力,而只是一种无意而为,自然流出的观念、意识。这些论述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,还有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的情感,似乎也是可以相通的。
与贴标签式的“四权束缚说”比,“封建礼教观念吃人说”,或者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说”,开始关注到了祥林嫂的精神被虐杀现象,这在小说意蕴层的揭秘上,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。但是因为偏重于外因的鞭挞,且不知不觉地将祥林嫂定位在恐惧而死,而忽略了更深层面的精神内因,从而也削弱了鲁迅作品对存在思考的深度与力度。
试想,祥林嫂如果内心的能量足够强大,这些观念,或者说无主名意识,又怎能奈何得了她呢?且不说这鬼柳妈没见过,祥林嫂没见过,即使这个阎王真的存在,也完全可以和他理论一番嘛!嫁给两个男人并非我的意思,我是想和第一个男人从一而终的,谁让阎王老爷您派人把他的魂勾走了呢?嫁第二个男人,纯属婆婆的逼迫,要清算也只能把帐记到她头上,跟我祥林嫂有什么关系呢?更何况,锯成两半,我就不是我了,怎么能陪伴两个死鬼男人呢?如果阎王还是不听,硬要锯,那就享受吧,无端地可以拥有一分为二的法力,同时过上两种生活,岂不快哉!如果作这样的推想,祥林嫂就不会被成见、偏见所束缚,反而能置之死地而后生,反弹出更加强劲的生命活力。可惜她没有!一听到这个子虚乌有的说法,立刻惴惴不安,神情恍惚,结果自我折磨,自我恐吓而亡。
如此,祥林嫂死于“自我折磨,自我恐吓”的说法,似乎又可以成立了!谁让她那么愚昧,那么胆小,那么死脑筋呢!
还有学者将祥林嫂的死因归结为“渗透于鲁镇社会的儒、释、道文化”,说在《祝福》里,无论是鲁四老爷书房里理学入门书(《近思录》)与传说中道教始祖陈抟老祖的朱拓“寿”联并存,还是岁末的祝福习俗与寡妇再嫁在阴间要遭分尸(人死以后,尸体或腐烂,或火化,还能分么?)酷刑的传说,以及土地庙捐门槛寻替身的庙规,无不“赋予鲁镇一种带有原始多神教意味且杂糅着儒、释、道多种成分的混沌性质”,正是这些最终吞噬了祥林嫂的生命。[⑤]北京大学孔庆东也持此说:“儒释道组成的礼教,到了民国后就退化了,礼教本来是个好东西,但好东西会耗散,能量散尽了之后就变成黑洞,就像天文学的黑洞一样,变成坏东西,要吞噬人。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祥林嫂是如何被封建礼教的黑洞吞噬的。”[⑥]
这些说法更让人摸不着北。祥林嫂的死与寡妇再嫁,在阴间要遭分尸酷刑的传说有关,这当然没有问题。但是,与《近思录》有关,和陈抟老祖的“寿”联有联系,还跟捐门槛寻替身有关,实在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事情。《近思录》一书主要谈“孔颜乐处”的圣人气象,格物穷理,存养心性之道,是“养生”“养心”,而非“害生”“戮心”,怎么就没来由地成了跨越时空的间接杀人犯了呢?祥林嫂倘若真的注意这方面的修炼,反而不会致死啊!陈抟老祖比较注重将黄老清静无为思想、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加以调和,写一个“寿”联,寄托了长命百岁的美好愿望,祥林嫂如果受其影响,心存顺其自然,或者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的念头,也断然不会轻易衰老,以致快速死去啊!如果相信门槛是自己的替身,可以躲过被锯成两半的厄运,更是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未来,活得极其淡定的啊!所以,“儒、释、道文化吃人说”,或“礼教黑洞吞噬说”,依然给人有隔靴搔痒,无法命中要害的感觉。
耐人寻味的是,尽管上述说法各异,但是“祥林嫂对阴间被分尸的恐惧”,则成了各家阐释祥林嫂死因,以及小说主旨的“交集”。祥林嫂死于一种心感、心造的压力、暴力,大家都没有疑义。但是,为什么这种心感、心造的压力、暴力致祥林嫂于死地,则没有做进一步地深入开掘。
在我们看来,祥林嫂死于希望的被剿灭!关于这一过程,鲁迅在《祝福》中作了极为充分地表现!
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,祥林嫂和其他女人一样有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的希望,可是天不遂人愿,丈夫很匆忙地撒手人寰。于是,祥林嫂的希望只能按照社会的惯例,降格为“从一而终,为夫守节”。她设法逃离婆家,到鲁镇打工;被捉,又以死抗婚,归根到底都是对这一微薄希望的持守。与贺老六生子,逐渐步入生活的常轨,说明她又滋生了做一个普通女人的希望:就像芸芸众生一样安安生生地过日子!可是,上天再次剥夺了她的这一希望:丈夫因伤寒而死,婚姻的结晶阿毛被狼吃掉。加上大伯的收屋,驱逐,她连独自在家中生活的希望也被彻底铲除。于是,她只能再次流浪。好在鲁四老爷家收留了她,让她有了一个存身之地。在鲁四老爷家二度打工的日子里,祥林嫂的希望更是低微、可怜——本能地一遍又一遍地描述儿子阿毛惨死的过程,其实只是渴望别人能听听就行。但这依然被扑灭——因为她后来再想开口讲述,人们已经很不耐烦,立刻会粗暴地打断她。
文中,鲁迅先生这样写到——
她还妄想,希图从别的事,如小篮,豆,别人的孩子上,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。倘一看见两三岁的小孩子,她就说:
“唉唉,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,也就有这么大了……”
孩子看见她的眼光就吃惊,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。于是又只剩下她一个,终于没趣的也走了,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气,只要有孩子在眼前,便似笑非笑的先问她,道:
“祥林嫂,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,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?”
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,早已成为渣滓,只值得烦厌和唾弃;但从人们的笑影上,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,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。她单是一瞥他们,并不回答一句话。
只是让别人听听自己诉苦就成了“妄想”“希图”,如此卑微的要求在祥林嫂心里竟然成了巨大的希望,却依然无法得到满足,社会的荒寒,人心的冷酷的确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祥林嫂竭力想从小篮,豆,别人的孩子等不同视角曝露自己的悲惨经历,人们非但已经懒得倾听,懒得安慰,反而掉过头来施以烦厌和唾弃。于是,她的那低到尘埃里的希望只能无奈地走向了灰飞烟灭。如果说丧夫、失子属于天灾的话,想倾诉而不得,就是人祸。努力越大,失望越大,伤痛就越深。
鲁迅通过这个细节,实际上已经将祥林嫂的物性处境很尖锐地揭示出来了。在鲁镇,祥林嫂充其量只是一个别样的玩物而已,她的悲剧性经历没有引起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同情,只不过是人们鉴赏、咀嚼以达到获得心理优越感的一种材料罢了。从鲁四老爷的皱眉,还有“谬种”之说,我们还知道:祥林嫂是属于不洁之物,甚至是不祥之物的范畴的,像骡马一样做点体力活可以,涉及年终祭祀之类的大事情,神圣事情,这样的人是不能让她染指的。如果将之视为作者的互文手法,那么鲁镇的其他人其实也是持这种想法的。这样,祥林嫂就无可避免地成为鲁镇中的一个异类,一个结构之外的人物,一如阿Q之于未庄,疯子之于吉光屯,魏连殳之于寒石山,只能是被观赏,被取笑,被打击,最终被歼灭。无论你是斗士代表,还是庸众一员,都难逃此厄。于是,环境成了异化人性,虐杀精神的象征物。
但就在这样阴郁、冷酷的环境中,祥林嫂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生之希望依然还存在,尽管已经日薄黄昏,气息奄奄!
她生之希望被凌迟的最后几刀,可以说来自柳妈嘴里的那个“死后被分尸”虚妄传说!四婶见祥林嫂要拿祭祖用的酒杯和筷子时,慌了神的一声大喊:“你放着罢,祥林嫂!”还有“我”为了“不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”,而借坡下驴说出的话“也许有吧”“论理,就该也有”。
这一过程,在小说中同样有极为清晰的呈现。
听了柳妈的话,祥林嫂“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”,“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,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。”本以为用两年左右辛辛苦苦赚来的工钱买了门槛,捐到寺庙当作自己的替身,可以万事大吉,没想到四婶的那句看似关怀,实际上却是朝心窝上捅刀子的一句话,使她一下子跌进了失望的万丈深渊。
关于这,小说也有极为详尽的描写——
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,脸色同时变作灰黑,也不再去取烛台,只是失神的站着。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,教她走开,她才走开。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,第二天,不但眼睛窈陷下去,连精神也更不济了。而且很胆怯,不独怕暗夜,怕黑影,即使看见人,虽是自己的主人,也总惴惴的,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,否则呆坐着,直是一个木偶人。不半年,头发也花白起来了,记性尤其坏,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掏米。
“祥林嫂怎么这样了?倒不如那时不留她。”四婶有时当面就这样说,似乎是警告她。
然而她总如此,全不见有伶俐起来的希望。
连解雇的威胁都感应不到,失望何其深!心何其痛!痛到沦陷死后被分身的恐惧中,不知抽身返归现实生活的地步,说明已经恐惧、失望得近乎麻木了。
但还没有彻底崩溃。真正的崩溃的是等到“我”的亲口回答之后。因为在祥林嫂眼中,我是“是识字的,又是出门人,见识得多”,所以最权威,最可信,但是阴差阳错,“我”误判祥林嫂的心理,本想帮她,却最终完成了剿灭祥林嫂生之希望的最后一刀。
因此,祥林嫂的死就成了必然!
柳妈出于取乐[⑦],四婶出于自私,“我”出于善意,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祥林嫂生命希望的最后屠戮,且以一种极为自然,极为家常的方式,很轻松地完成。这恰恰是看似闲淡的笔墨,却让人心灵无比惊悚的主要原因,因为其间隐藏了鲁迅极为悲愤和痛苦的人生体察。但丁在《神曲》中对地狱之门上的铭文有这样的描写:“你们走进这里来的,把一切希望都捐弃了吧!”[⑧]这其实暗喻了一个无比深刻的人生哲理:对一个人最残酷的惩罚,不是凌辱他的肉体,毁灭他的生命,而是剥夺他的希望。鲁迅通过祥林嫂这一形象的塑造,恰好传递了这种人生通感!
“我”之所以“愧疚”“不安”,有“不详的预感”,也正是由于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也参与了对祥林嫂希望的围歼——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。待证实祥林嫂的死讯后,他的心更为沉重了。爆竹的钝响,天空的昏沉,实际上正是他沉重心情的投射。为什么所有的鲁镇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独独“我”意识到了?这在文中其实已有伏笔交待,说“百无聊赖的祥林嫂”,是“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,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”,可是“我”不同,因为我将祥林嫂视作了“人”,甚至是“灵魂的审判者”。这种忏悔和反思,混合着“我”对现实和自我的绝望,与祥林嫂的绝望人生恰好形成了小说的复调,非常有力地展现了生命希望泯灭的悲哀与凄凉。
沿着这样的理路去思考,祥林嫂没被鲁迅刻画成和阎王对峙的真正烈女,也没被刻画成圆滑、世俗,精于算计的女性(不让我帮忙,我就趁机歇着,养养神也好嘛),或者很冷静,很有头脑的女性(柳妈的话靠谱吗?既然靠谱了,我又何必介意女主人的看法呢?再说,那个见识多的知识分子也对阴间的有无拿不准,我何必自寻烦恼呢),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
说到底,祥林嫂尽管有时很清醒,又很尊严,比如她从人们的笑影上,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,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。她单是一瞥他们,并不回答一句话。但从本质上说,她其实是个一直生活在别人思想、言说中的人。比如说,起先深信柳妈的“死后被锯”说,信到什么程度?连失子之痛都消失了,或者说被柳妈的可怖描述覆盖了。但是,当她捐了门槛作为自己的替身,以为可以近神、祭祖,却被四婶断然阻止时,她再次跌入恐怖的深渊。这说明,相对于柳妈,四婶的想法更为可信。但是见到“我”的踪影,垂垂朽矣的她毫不犹豫地迎了过来,眼睛竟然是“瞪着”的,这说明“我”才是她心中可怖谜团的终结裁定者,只因“我”是“出门人”“见识多”。信来信去,唯独没有信自己。这就是祥林嫂!一个愚拙而善良,内向而烈性,强韧而脆弱,痴情而清醒,清醒而混沌,混沌而简单,简单而复杂的普通女性!鲁迅着意将她这种心理深层的意识挑破,显然有一种无比痛苦的发现:这是一个小如微尘,贱如奴隶的平凡生命的悲剧,一个微薄、寻常的希望被践踏,被蚕食,被凌迟的悲剧!可是当事人自己,也参与了自我生命希望的屠戮!因为没有将罪全部推在封建礼教观念,或者说儒释道文化上,使它们成为一种单一化的吃人象征物,所以希望死灭的过程就更加充满了悲剧性!
说祥林嫂死于希望的死灭,还可以从小说暗示的春天意象中见出。
“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”;是“新年才过”被婆婆请出的人绑架的;儿子阿毛是春天的清早被吃掉的;最终死于迫近新春的年终。春天,草长莺飞,万紫千红,最富生机,最富希望的季节,可是卑微如草芥的祥林嫂在四十上下的生命盛年,却无权享用,只能被动地丧失希望,被动地丧失生机,无可奈何,满怀恐惧地走向死地。
以乐景写哀,此为其一!
其二,祥林嫂的希望最终走向死亡,被设置在了一个极其热闹,极其欢快的气氛中。“送灶的爆竹”声响不断,“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”;家家户户在忙着“杀鸡,宰鹅,买猪肉,用心细细的洗,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,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”,堪称“活得有趣”。可是,祥林嫂在这样的喜庆氛围中很不知趣地死了!以致她要么被忽略,要么被视为“谬种”。即使她那年轻而衰败的僵硬尸体,还有那双被绝望和恐惧填充而无法闭上的眼睛,能向天地发出无声的呐喊与抗议,也会很快被“团团飞舞的雪花”掩盖,“被无常打扫得于干净净了”。
最后不妨来看看题目《祝福》,谁在祝?
是芸芸众生么?用烹熟的“福礼”向福神拜求来年的好运气。可是,面对身边同伴的死亡,不闻不问,却丝毫不担心报应之说,或者神灵怪罪!这样的功利、自私、怪胎的祝福,神敢悦纳么?
是“天地圣众”么?在“歆享了牲醴和香烟”后,“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,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”,可是面对惨死户外的子民,却闭上祝福的双眼,岂不正好验证了阎王的盲目和蛮横?这样的祝福,真正有头脑的人,谁信呢?
因此,题目与意象、氛围等一起,也构成了一种反讽,不仅道出了人情冷暖,世态炎凉,也寄寓了鲁迅对希望死灭的椎心泣血的思索。联系《药》《故乡》《明天》《在酒楼上》《孤独者》等众多作品,我们不难发现,对生命希望的思索,对人性乌托邦的守望,鲁迅从未终止过。虽然他也说过“绝望之为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”,透着一种无边的悲凉,但是他同时也承认“说到希望,却是不能抹杀的,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”[⑨],所以不论是写希望的萌生,如夏瑜坟头上的小野花,还是对“走得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的自励,甚至是将希望的被毁灭清晰地呈现给人看,如单四嫂子、祥林嫂希望凋零的表现,都体现了他以希望反抗绝望,在绝望中种植希望的艰难努力。
从这个角度说,鲁迅描写祥林嫂生命的毁灭,就不是仅局限于对冷酷社会的揭露,对丑陋国民性的鞭挞,对封建礼教野蛮吃人的控诉了,因为其间还分明包融了他对荡涤伪饰陋习,冲破生存“铁屋子”的庄严思考,对“致吾人于美善刚健”[⑩]的叩问与探求,对人性乌托邦的苦苦守望……这或许正是他的思想超拔常人的敏锐与深刻之处吧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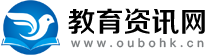
![[2015北京高考生物]2015优秀生物摄影作品4](http://img.zxxk.com/2015-10/ZXXKCOM201510281610518248436.jpg)


![[2015北京高考生物]2015优秀生物摄影作品2](http://img.zxxk.com/2015-10/ZXXKCOM201510281600000371162.jpg)
